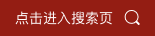本文系2016年黄宗智教授研修班学员陈瑞琳所撰,被遗漏至2018年10月1日才发现,特此补发。
上黄老师的课,对我来说,是一次惊心动魄的体验。在过去的一个月,我边阅读边处理其他的学习事务,度过了最繁忙也最充实的一个暑假。为了写这一份课程感想,我又重读了自己撰写的读书笔记。各种阅读的感受和思考仍然鲜活,历历在目,自己也仿佛边理清思绪边重温了这一次经历。
最开始知道这门课程是通过一位老师,他告诉我,黄老师是有名的华人历史学家,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有自己的风格,非常值得我学习。在这之前,我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,中文写作常常觉得词不达意,英文阅读又平添中英转换的难题,所以我最初申请这门课程,是希望加强自己的学术写作能力并了解黄老师对中国农民的看法。
得知自己被录取当然是非常兴奋的。那个时候我正好也应邀去参加日本的一个暑期夏令营,虽然因为时间冲突错过了这个夏令营,但是开始上黄老师的课之后,我便知道,一切都是值得的,而且一切都是远超预期的。
黄老师就像老师傅给小徒弟传授武艺一般,将自己毕生的感悟悉数告诉我们。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会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,提到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影响了他的学术风格,也说起自己的本科求学之路。在各种光环的影响之下,人们很容易将研究者符号化,将他们的作品和学术研究神秘化,黄老师用他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,学者首先是人,选择的研究话题、善用的研究方法,也都带有个人色彩,学术研究本身则是一个智力与情感交融的过程。多年的经济学教育让我几乎忘记了人的主体性,重新记起这一点对我自己的学术之路尤为重要,它让我更加忠于内心,也不再害怕代入个人感情,开始着手去寻找适合我的研究问题。
在课程开始之前,我曾非常担心自己是否会跟不上进度。我从本科到研究生学的都是经济学,阅读面非常窄,只是从一门经济史的课上知道了黄老师的名字,之前也并没有看过他的书,更不用说《东方学》、《实践感》等了。这些书名在我看来非常陌生,讨论的问题也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,我很怕自己会理解不了,也无法跟上课程讨论。
上了课才发现,这些担心是多余的。在课上,我们每周集中阅读一到两本书,然后撰写读书笔记。阅读本身是困难的,但并非完全无法完成。我自己天资愚笨,每次要花三天或者更多的时间反复看好几遍才能看懂一本书、理清它的脉络。但这并不是最困难的部分。写笔记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挑战。本来就词不达意的我,常常要花上好长时间斟酌和修改一份笔记,才觉得满意。但是这显然是必要的学术训练。黄老师在课上告诉我们要学会分辨什么是必要的学术包装,什么才是核心的论点,如果不看《法律社会学》和《实践感》,我想我不会了解这一点的含义。在理解和整理复杂论点的过程中,我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这一切当然离不开黄老师的帮助。他每次都会帮我们批改读书笔记,也会在课上引导我们加深对著作本身的理解,纠正我们的错误。课程小伙伴之间也常常会交换读书笔记。因此,整个学习和阅读过程都是非常立体的。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是一个人在挑灯夜读,但是每个星期都能与大家讨论一次,在我看来,这才是整个阅读体验的最高潮,像极了秋割时的热闹和丰收。
但这还不是全部。除了技巧之外,黄老师还向我们传授了一整套学术之道。研究几十载,也亲身经历了学术界在研究方向上的几次大转变,黄老师在何为好的研究这个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个人见解。他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,年轻人容易被理论吸引,但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沉迷于理论,而要从最丰富的一手资料入手积累经验事实,遵循“经验-理论-经验”的思路,而不是理论为先导,先有理论再去寻找经验证据。他还强调不要做普适的东西,要关注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;要关注不同理论的交锋,不要成为某一个理论的拥趸者。对我来说,这些建议出现的非常适时。在我做出重大决策之前,黄老师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以前的研究思路所存在的问题,让我看到了潜藏的危机。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博士生涯的规划,以前的我太习惯于做理论推演,太习惯于理论为主经验为辅,也太受特定流派的影响,这极大的限制了我的视野。
历时一个月的课程已然结束,但是我的阅读量反而增加了。我开始更多的接触其他领域的文献,并决定将主动阅读的方法践行下去。我仍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研究之路,但是这一次,有了黄老师传授的武林秘籍,我想我能做的更好。